屏幕的光在凌晨三点显得格外清醒,我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,指尖却停不下来,一条,又一条,关于那个名字的讨论像潮水一样涌进视线,其实我早该睡了,明天还有早会,可眼皮沉甸甸的,手指却有自己的意志。
起初只是好奇,晚饭时刷到那条语焉不详的热搜,配图是模糊的街角,两个挨得很近的影子,评论里已经吵翻了天,有人信誓旦旦,有人嗤之以鼻,我划过去,没在意,碗筷收进水池时,水龙头开得有点大,溅湿了袖口一小片,凉意透过布料贴上来。
真正开始找,是洗完澡之后,头发湿漉漉地搭在肩上,毛巾有一搭没一搭地擦着,我靠在床头,重新点开那个词条,这次看得仔细了些,那些所谓的“证据”——同款外套出现的时间差,行程表上空白的三个小时,一张被放大到像素模糊的餐厅玻璃反光,真可笑,我想,指尖却往下滑,点进了一个分析帖。
楼盖得很高,发帖人用冷静到近乎刻薄的语气,把时间线拆解得像数学证明题,下面跟帖的人越来越多,补充着各种边角料:他助理那天戴的帽子,她经纪人突然删除的微博,某个综艺里一句当时没人注意、现在回味无穷的玩笑话,我看着那些字,一个个跳进眼睛里,房间里只有空调低沉的送风声,和我自己的呼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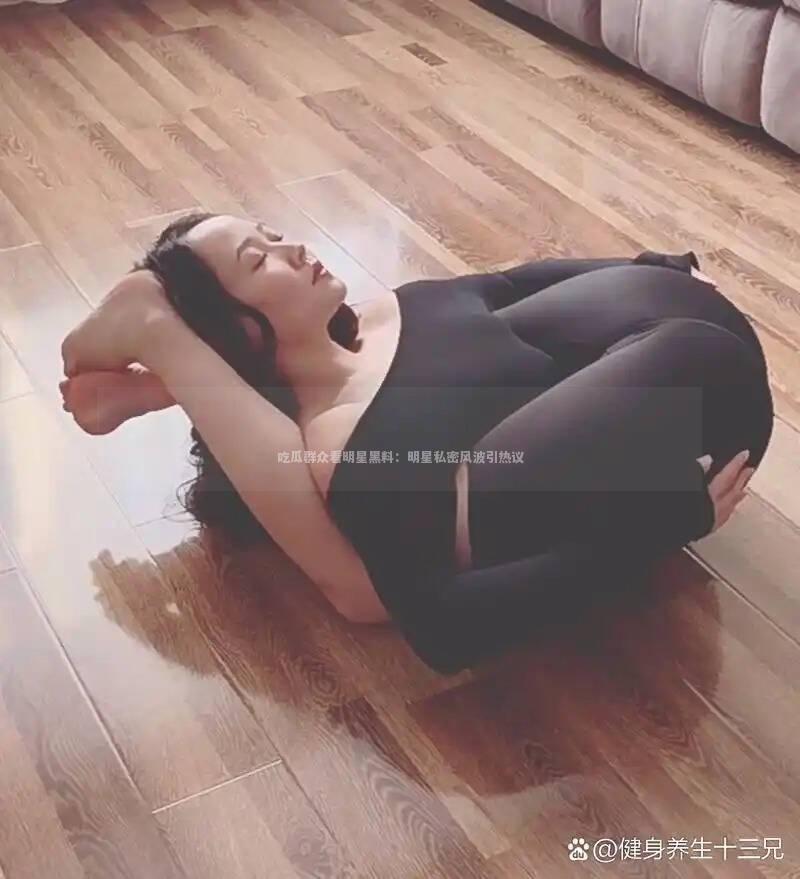
不知什么时候,我把腿蜷了起来,下巴搁在膝盖上,这个姿势让后背有点酸,但我没动,屏幕的光映在脸上,应该是一种不太健康的青色,我又点开另一个链接,这次是视频剪辑,把两人过去一年所有公开场合的同框镜头拼在一起,背景音乐是某首很老的英文情歌,调子慢悠悠的,画面里他们有时对视,有时错开目光,有时在人群两端,却好像朝着同一个方向。
我按了暂停。
浴室镜子上还蒙着一层未散尽的水汽,我站起来,走过去,用手掌抹开一小块清晰,镜子里的人眼睛有点红,不知道是困的,还是别的什么,我拧开水龙头,用冷水扑了扑脸,水珠顺着脖颈流进衣领,激得我轻轻一颤。
回到床边时,手机屏幕已经暗了,我犹豫了一下,没有点亮它,躺下来,盯着天花板,黑暗里,刚才看过的那些画面、那些句子,却自己浮上来,那些被无数人咀嚼、分析、赋予意义的瞬间,那些可能什么都不是的巧合,我想起去年秋天,在电影院昏暗的光线里,旁边座位的人伸手拿爆米花时,手指无意间擦过我的手背,就那么一下,电影里在演什么,我后来完全想不起来了。
手机突然在枕边震动了一下,我几乎是立刻抓起来,却只是一条软件推送,屏幕亮起的光,短暂地照亮了房间一角,照亮了搭在椅背上那件他的衬衫,我盯着那团模糊的阴影看了几秒,然后按灭了手机。
第二天上班,地铁挤得像沙丁鱼罐头,我戴着耳机,但没放音乐,旁边两个女孩在热烈地讨论昨晚的“新发现”,声音压低了,却压不住那种兴奋。“你看那张图了吗?窗帘的花纹都对得上……”我往旁边挪了半步,玻璃窗上倒映出自己没什么表情的脸。
一整天,效率低得可怕,文档上的字飘来飘去,中午休息时,我又鬼使神差地点开了那个已经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论坛,新的“锤”出现了,是一段据说是私人聚会的录音,音质嘈杂,听不真切,但标题用加粗的红字写着“实锤!本人声音对比!”,我没有点开播放键,只是看着那个红色的三角形图标,看了很久,茶水间的咖啡机发出沉闷的咕噜声,一股焦苦的味道弥漫开来。
下午开会时,我走了神,经理在讲什么季度数据,幻灯片一页页翻过去,我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,想起那个视频剪辑里的某个镜头:她说完一句话,低头笑了,而他正好看过来,目光在她侧脸停留了可能不到一秒,就那一秒,被慢放,被循环,被几十万人观看、解读、判定。
下班路上,我去超市买了菜,经过杂志架时,瞥见一本娱乐周刊,封面正是那两张熟悉的脸,标题巨大而暧昧,我推着购物车走了过去,在生鲜区挑了几个苹果,手指按在果皮上,能感觉到那种饱满的、紧绷的硬度。
晚上,我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,自己在书房整理旧书,纸页泛着淡淡的霉味,中间夹着一张很久以前的电影票根,字迹已经褪得几乎看不见了,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片,站了一会儿,窗外有车灯的光扫过,很快又暗下去。
临睡前,我最后看了一眼手机,那个话题还挂在热搜上,后面跟着一个“爆”字,点进去,风向似乎又变了,开始有人质疑证据的真实性,有人呼吁理性吃瓜,各种声音吵吵嚷嚷,像一锅煮沸的水。
我关了灯。
黑暗彻底落下来,这一次,我没有再想起那些模糊的街拍、那些分析帖、那些被慢放的凝视,我只是听着自己的呼吸,慢慢沉进枕头里,远处隐约传来夜班公交驶过的声音,由近及远,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明天太阳升起时,会有新的话题,新的潮水,而此刻,只有床头充电器上,那一点微弱的、红色的光,在规律的明灭之间,映着空无一物的墙壁。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