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盯着屏幕,指尖悬在发送键上方,像悬在悬崖边,房间里只有空调低沉的嗡鸣,皮肤能感觉到那种均匀的、人造的凉意,但胸腔里却烧着一团黏稠的东西,不上不下,聊天框里,那个她反复编辑又删除的句子,最终还是以最简短的形态存在着:“你看了吗?”
“看了。”对方回得很快,快得让她胃部一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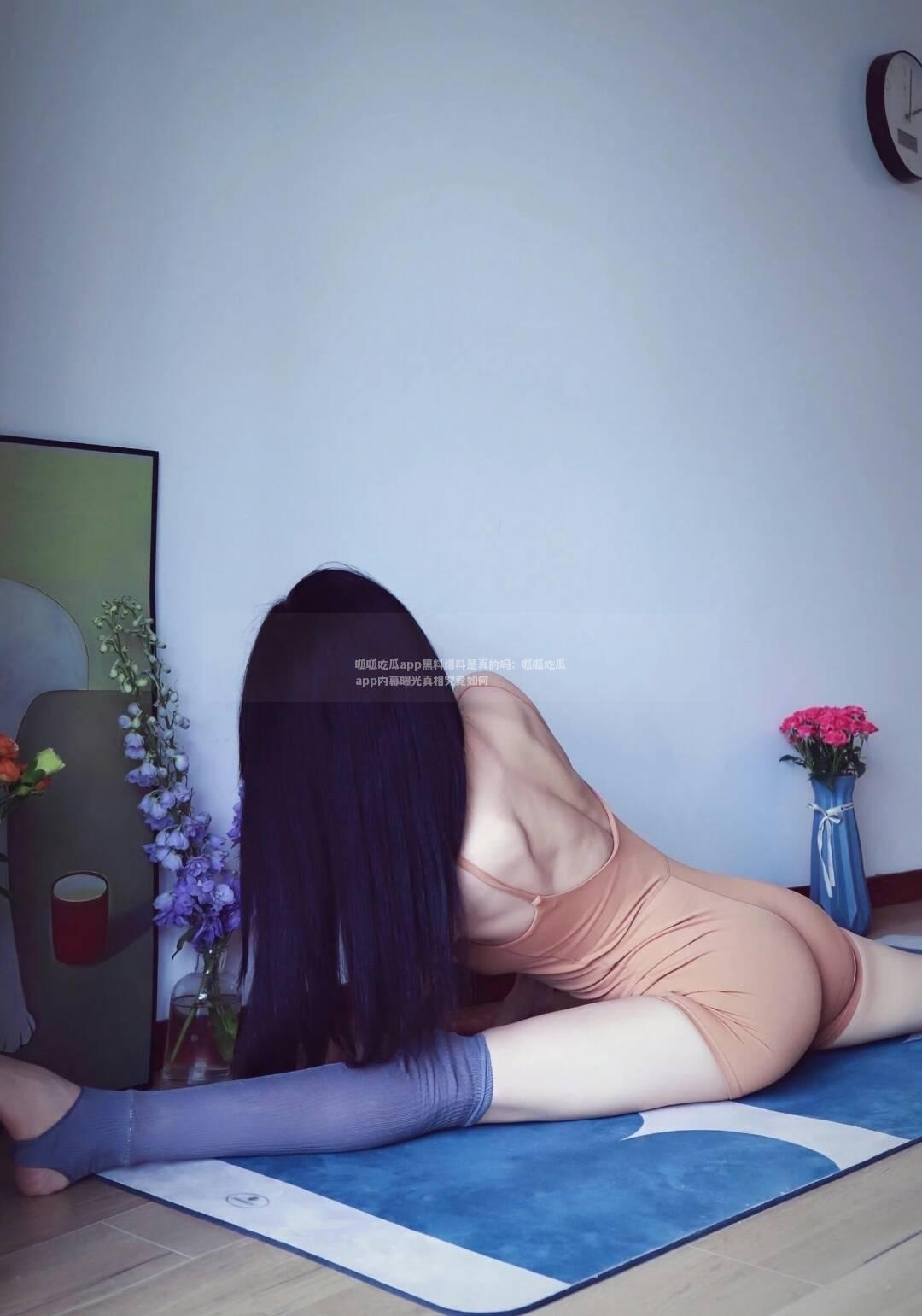
然后是漫长的“对方正在输入…”,那行字跳动着,像某种不祥的心率,她移开目光,看向窗外,下午四点的光斜斜地切进来,把地板分成明暗两半,灰尘在光柱里缓慢翻滚,无声无息,她就在那暗处,手机屏幕的光,是这暗处唯一活着的、刺眼的东西。
终于,消息来了,不是文字,是一张截图,来自那个叫“呱呱吃瓜”的界面,一个她熟悉到能背出布局、却又在此刻陌生得令人作呕的角落,截图里,有她的背影,模糊,但认识她的人,一定能认出来,配文是几个意味不明的表情符号,和一句:“猜猜这是谁?深夜福利。”
她没猜,她知道,那个夜晚的空气湿度,那条裙子摩擦小腿的触感,电梯镜子里自己疲惫又带着某种决绝的眼神,还有……身后那道若有若无、却始终黏着的视线,原来不是错觉,原来那个“福利”,被这样定义,被这样切割,被放在那个充斥着戏谑评论和虚拟货币打赏的橱窗里。
她没哭,愤怒像一块干冰,嘶嘶地冒着白气,把眼泪都冻住了,她甚至有点想笑,笑自己那天出门前,还对着镜子犹豫过口红的颜色,太可笑了,你精心涂抹的,不过是别人眼里可以标价出售的色块,你小心翼翼维护的某种体面,在另一些人手中,轻易就能揉碎,变成猎奇的碎片,供人咀嚼、吞咽、然后排泄。
她开始翻那些爆料帖,手指滑动得很快,快得几乎看不清文字,只捕捉到一些关键词,一些缩写,一些心照不宣的暗语,真真假假,混在一起,有人说这是内部人员流出的,有人说是黑客所为,有人信誓旦旦说认识当事人,每一个“据说”,每一个“我朋友说”,都像一根细小的针,扎进她已经麻木的皮肤,不很痛,但密密麻麻,让人坐立难安。
她看到其他女孩的故事,有些打了厚厚的码,有些没有,有些叙述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,有些则充满了激烈的、几乎要冲破屏幕的控诉,她一篇篇看下去,像是在照一面面破碎的镜子,每一片碎片里,都有一个变形的、被窥视的“她”,那些被偷拍的瞬间,被曲解的对话,被恶意揣测的动机……它们不再是孤立的新闻,它们连成一片潮湿的、窒息的网,她就在网中央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,是那个朋友。“你还好吗?”后面跟着一个拥抱的表情。
她盯着那个拥抱的符号,看了很久,虚拟的体温,她打下“没事”,发送,怎么可能没事,但说“有事”又能怎样呢?换取另一轮小心翼翼的安慰,或者,更糟糕的,勾起对方隐秘的好奇?她甚至能想象出屏幕那边,朋友复杂的神情——同情里混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寻,想知道更多细节,又为自己的想知道感到些许羞愧。
她关掉聊天窗口,点开那个App,图标很可爱,一只绿色的卡通青蛙,咧着嘴,她曾经觉得它挺有趣,那些无伤大雅的八卦,碎片化的娱乐,是地铁上、排队时打发时间的糖果,现在,这只青蛙的嘴,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,她点开自己的浏览记录,一条条删除,又去设置里,注销账号,流程很顺畅,没有任何挽留,只有一个冰冷的提示:“账号注销后,所有数据将被清空。”
清空,这个词让她感到一阵虚脱般的轻松,随即是更深的空洞,数据可以清空,那些被截取的影像,被传播的碎片,被无数陌生眼睛浏览过的“她”,能清空吗?它们像病毒,潜伏在网络的毛细血管里,也许此刻,就在某个她永远不知道的群组,某个匿名的论坛,被再次转发,配上新的、更不堪的注解。
黄昏彻底吞没了那半片光亮,房间沉入均匀的昏暗,她没有开灯,黑暗像水一样漫上来,包裹住她,皮肤上的凉意变得真实了,她抱住自己的胳膊,指甲无意识地掐进肉里,留下浅浅的月牙印。
她想起很久以前,大概是童年,有一次在河边玩,看见水底有一片特别亮的瓷片,阳光透过水波,把它照得闪闪发光,她伸手去捞,捞上来才发现,那不过是普通碎瓷碗的一角,边缘锋利,割破了她的手指,血滴进河里,很快就被冲淡,不见了,水还是那么绿,那么平静,映着天光云影,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现在,她就是那片被捞起来的碎瓷,离开了原本沉没的、不被看见的黑暗水底,暴露在天光下,被人掂量,被人评论,被人赋予各种她从未想过的意义,而那片水,那个App,那个由无数视线和话语构成的巨大存在,依然平静地、绿汪汪地存在着,映照着下一个人的天光云影。
手指上的旧伤疤,早就不疼了,但那种被锋利边缘瞬间划开的触感,冰凉,清晰,带着一种诡异的确定感,却好像一直留在神经末梢。
她终于动了动,不是因为想通了什么,而是坐得太久,身体发出了僵硬的抗议,她站起身,走到窗边,楼下街道,车灯汇成流动的河,霓虹次第亮起,世界按照它既定的、热闹的节奏运转着,没有人抬头看这扇漆黑的窗户。
她不知道那些爆料是不是“真的”,真的,又如何呢?假的,又如何呢?当一种伤害已经发生,当一种凝视已经穿透皮肤,抵达骨髓,去争论那凝视的载体是否合法,是否“有实锤”,就像在火灾现场争论最初的火星来自火柴还是打火机。
重要的是,房子已经烧着了,她站在废墟里,闻着灰烬的味道。
手机屏幕在身后的沙发上,又微弱地亮了一下,旋即熄灭,可能是推送,可能是广告,也可能是别的什么,她没有回头去看,她只是看着窗外,那片由无数灯火、无数窗口、无数正在发生和已经湮灭的故事组成的,庞大而无言的夜。
风从窗缝挤进来,吹动她额前的碎发,有点痒,她抬手,轻轻拨开,一个极其日常的,属于活着的身体的,微不足道的动作。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