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总觉得那目光还黏在背上,像一层没擦干净的糖浆,缓慢地渗透进衣料与皮肤之间的缝隙里,不是灼热的,甚至谈不上专注,只是一种温吞的、持续的存在,恰好卡在她能感知的边缘,她调整了一下坐姿,脊椎一节一节地往下沉,试图让肩胛骨更贴合椅背的弧度,仿佛这样就能把那道无形的视线挤出去,可它还在,随着她呼吸的起伏,轻微地调整着角度,仿佛她是一页需要被仔细阅读、却又不必急于翻篇的文字。
空气里有种过于洁净的味道,消毒水底下藏着陈旧的木头与纸张的气息,混合成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严肃,她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面前纸张的边缘,触感平滑而微凉,这动作本身毫无意义,只是为了让身体某一部分保持一种看似合理的动态,以掩盖其他部分近乎僵硬的静止,她能听见自己吞咽的声音,在过分安静的室内显得突兀而潮湿,每一次喉头的滚动,都像是对某种寂静协议的背叛。
那目光似乎移动了,从肩胛滑向了颈侧,她颈后的皮肤起了一层细密的颗粒,不是寒冷,而是一种被缓慢加热的警觉,她不该去确认的,她知道一旦转动视线,哪怕只是眼角的余光,都会立刻坐实这份在意,将暗处的拉扯暴露成明处的交汇,可脖颈的肌肉却开始酝酿一次微小的、几乎无法察觉的偏转,仿佛自有其意志,被那无声的牵引力拉扯着,她用力咬住了口腔内侧的软肉,一丝铁锈般的腥甜漫开,疼痛像一根细针,暂时钉住了那蠢蠢欲动的念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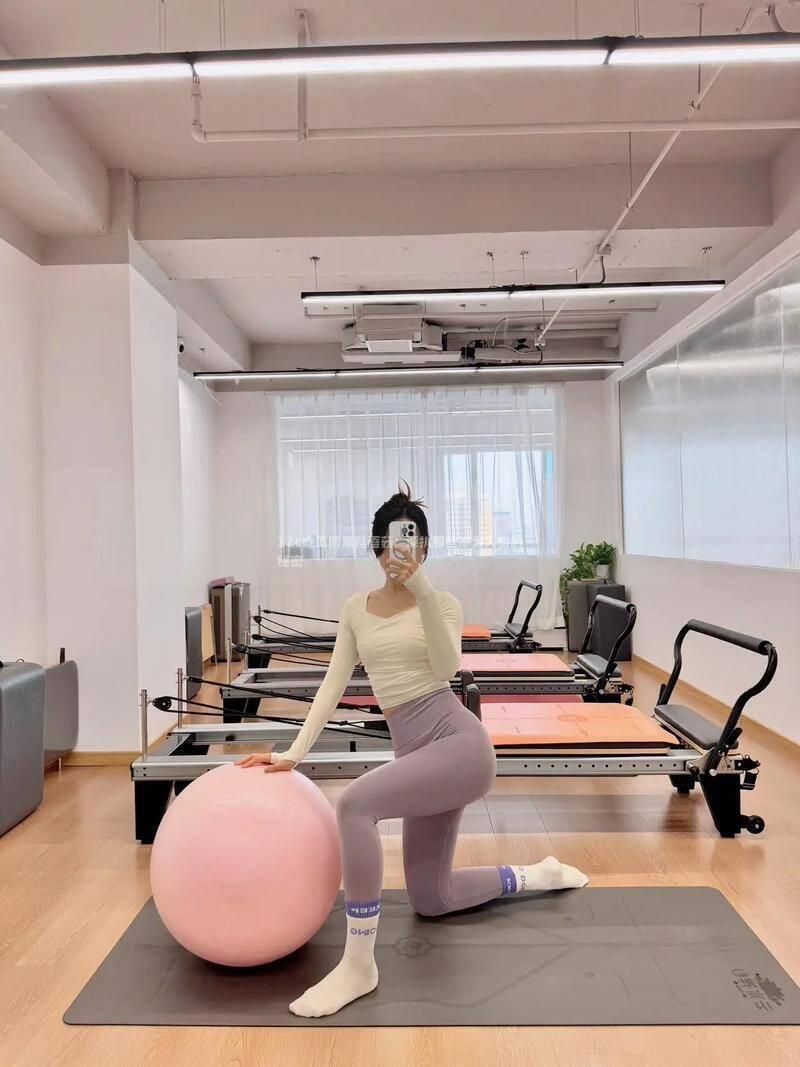
期待像水底的暗流,在她刻意压平的思绪之下蜿蜒,她厌恶这期待,因为它毫无来由,又因为它过于具体——具体到能勾勒出那目光可能的形状、温度,甚至它移开时可能留下的短暂空白,这空白比注视本身更令人难堪,那意味着她成了被衡量、被暂时搁置的物件,她开始数自己的呼吸,一,二,三……数字在脑海里变得绵软而粘稠,失去了清晰的边界,每一次吸气,都像在胸腔里灌满了那种温吞的、糖浆似的空气。
她忽然对桌上那支笔的摆放角度产生了难以忍受的在意,它斜躺在摊开的笔记本旁,银色的笔帽反射着顶灯惨白的光,那光斑像一只冷漠的眼睛,它不该那样摆着,那角度透着一股漫不经心的挑衅,她想把它摆正,让它的长轴与笔记本的边缘平行,形成一种严丝合缝的秩序,这个念头毫无道理地强烈起来,几乎要压过背上的视线,指尖动了动,悬在纸张上方几毫米处,犹豫着,去调整一支笔,这个动作太小,小到可以解释为任何无关紧要的习惯;又太大,大到可能成为打破整个脆弱平衡的第一个裂隙。
寂静在膨胀,她能听见远处隐约的、被墙壁滤过的交谈声碎片,像隔着水传来的模糊响动,而近处的静,则有了重量和密度,压迫着鼓膜,那目光似乎也成了这寂静的一部分,一种有形的、沉默的询问,或者更糟,一种有形的、沉默的等待,等待她先露出破绽,先做出那个可以被定义为“反应”的动作,她的胃部微微收紧,一种下坠感从腹腔深处蔓延上来,这不是恐惧,更像是一种站在极高处俯瞰时,身体本能产生的虚空引力。
她想起一种触感——不是此刻的,是记忆里某种被捂得太久、变得潮湿而温热的皮革,那触感毫无征兆地浮现,带着令人不适的亲昵,贴附在对手腕内侧皮肤的想象上,她立刻驱散了它,像拂去一粒看不见的灰尘,可那想象的余温却残留着,让腕部的脉搏跳动得更加清晰可辨,一下,又一下,敲打着那并不存在的皮革束缚。
那目光终于移开了,不是骤然抽离,而是一种缓慢的、几乎带着倦意的滑脱,从她颈侧滑向虚无的空气,背上那糖浆般的粘滞感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陡然降临的、微凉的轻松,以及紧随其后的、更深的不安,仿佛一直支撑着她的某种无形的压力突然撤走,让她晃了一下,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重心,轻松是短暂的,像气泡一样破裂,不安则沉淀下来,淤积在心底,因为移开本身,就是一种更复杂的讯号,它意味着观察的暂时满足,或是兴趣的转移,又或者,仅仅是一次蓄意的停顿,为了下一次更精准的捕捉。
她依旧没有动,笔还是那样斜躺着,反射着那片冷漠的光,呼吸渐渐平复,但胸腔里却像被那淤积的不安填满了,沉甸甸的,室内的光线似乎暗了一分,阴影从家具的角落悄悄爬出来,拉长了形状,那被目光抚摸过的皮肤,此刻才真正开始苏醒,泛起一阵迟来的、细微的刺痒,仿佛有看不见的丝线刚刚从那里抽离,留下了微不足道却无法忽略的痕迹,寂静不再是压迫,而成了一种空旷的、回响着什么的容器,她在里面,等待着那或许会再次落下的视线,也等待着那或许再也不会到来的下一次触碰,空气里的洁净味道,此刻闻起来,只剩下空旷的冷。





